《同义词》剧情介绍
同义词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约亚夫(汤姆·梅西尔 Tom Mercier 饰)是一名以色列退伍军人,他非常向往法国浪漫而又开放的风气,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结果却惨遭打劫,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对艺术家情侣卡洛琳(昆汀·多尔马尔 Quentin Dolmaire 饰)和艾米勒(露易丝·谢维洛特 Louise Chevillotte 饰)向约亚夫伸出了援手,令他免于流落街头的厄运。 经此一劫,约亚夫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拒绝再说母语,通过背同义词的方式学习法语。很快,约亚夫就发现,卡洛琳和艾米勒虽然对自己表面友善,但其实是在利用他。约亚夫在战场上的悲惨经历成为了艾米勒创作的养分,而卡洛琳则试图通过约亚夫强壮的身体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性欲。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冲击波姐妹的梦魇动物王国十二宫骑士:圣斗士星矢象州风云下一个台风可爱的骨头嬉皮未成年天娇给你生命给我爱听见颜色的女孩龙卷风末日国宝疑云一点点欺骗:汉娜·斯文森之谜冷静与热情之间西辛8鳄鱼群功夫美男无与伦比的美丽纠缠1899朕的刺客女友无间行动附身荣耀三九年无懈可击对面的夜我是传奇黑暗中的猎手左轮手枪
约亚夫(汤姆·梅西尔 Tom Mercier 饰)是一名以色列退伍军人,他非常向往法国浪漫而又开放的风气,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结果却惨遭打劫,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对艺术家情侣卡洛琳(昆汀·多尔马尔 Quentin Dolmaire 饰)和艾米勒(露易丝·谢维洛特 Louise Chevillotte 饰)向约亚夫伸出了援手,令他免于流落街头的厄运。 经此一劫,约亚夫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拒绝再说母语,通过背同义词的方式学习法语。很快,约亚夫就发现,卡洛琳和艾米勒虽然对自己表面友善,但其实是在利用他。约亚夫在战场上的悲惨经历成为了艾米勒创作的养分,而卡洛琳则试图通过约亚夫强壮的身体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性欲。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冲击波姐妹的梦魇动物王国十二宫骑士:圣斗士星矢象州风云下一个台风可爱的骨头嬉皮未成年天娇给你生命给我爱听见颜色的女孩龙卷风末日国宝疑云一点点欺骗:汉娜·斯文森之谜冷静与热情之间西辛8鳄鱼群功夫美男无与伦比的美丽纠缠1899朕的刺客女友无间行动附身荣耀三九年无懈可击对面的夜我是传奇黑暗中的猎手左轮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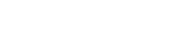
can't relate at all
莫名其妙。不明白他最后的愤怒是哪来的?按照中国人的逻辑,落难之时的帮助是有恩之人,不求报答也不至于仇人相向吧?你自己想当男模,让人侮辱了一通,你对朋友发什么火?!就你那破故事还收回?前边还对老婆温柔脉脉,转眼就跑人家单位闹一通。跟那个四处挑衅的以色列傻逼一样无理取闹。
导演不能找个颜值高的嘛,男主真的是太丑太丑了,长那么丑跑出来当什么演员,融不进去就是融不进去,不如趁早回家种地
一个关于“身份”的寓言,关于犹太人,也关于当今欧洲,退伍士兵离开以色列无疑是对以色列穷兵黩武和狭隘民族意识的反击,他要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在巴黎,打开字典,说出最地道的法语,但他仍然被困于迷宫之中,那些过去的记忆,伴随着《特洛伊》中赫克托耳的故事,欲说还休,在以色列移民和法国人之间摇摆,三角关系,高唱《马赛曲》和重新说出希伯来语,文明的假面之下,当下欧洲的危机,不仅是话语与现实的落差,更是内心偏见与狭隘道德的共谋,拉皮德在巴黎完成了对祖国的对话,以色列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孤岛,压抑的、沉闷的、禁锢的、堕落的,交出自己的语言,交出自己的行李,交出自己的身体,最后呢?他仍然不属于这里,婚姻也不能赋予身份,大使馆同样不能,只有带着自己的故事离开,那扇门永远地对他关闭了,里面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只是伪装
一部露某器官比之露同性之好更肆意的电影,他来自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国家,他手持一本法语字典,念着那些意思相近的连绵不绝的单词,他咆哮,他怒吼,他热烈地亲吻,就差一丝不着在大街上抬头挺胸了,可终究他不是法国的一员。
荒诞派吗?改名等待秃头歌女吧
奇妙的观影体验,低头与抬头,狂乱的手持。感觉背景如果换到美国会更有意思
男主躺下,我就想坐上去;男主站起来,我就想蹲下去;男主远景,我就想扑上去;男主特写,我就想亲上去。
有很多荒诞、尴尬又脱线的情节,会造成困惑突兀的观感(尤其是叙事不时断裂)但细想一下又觉得可能是需要这么安排的。因为他的存在从一开始便是格格不入,就如他的醒目黄色大衣、他毫无保留的裸体,或是他在舞池里叼着的面包那样。少许同性情感描写很微妙,彼此交换着眼神与故事。不只是通过两国语言的习得与拒绝,他的身体也(被动地)成为他融入异国的工具。最终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声声不甘而徒劳的撞击,这道border始终都在且无法逾越。
想成为法国人的疯狂以色列人。如果视为反战片,三角恋这角度也太特别了。
如果有人呐喊,他们就演奏乐曲
系统的补一句:完全无法有代入感的沉浸。电影在主客观视角自由切换,在身体语言诸多符号之间自由切换;在世俗领域,导演是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异乡人,在精神领域,又是手握话语权虚荣无力的知识分子。复杂的身份和现实技巧共同编织的精巧小品,接受放弃共情的间离感,但在趣味和聪明之外的启发感无法满足。
(8.4/10)不止一次让我想到《方形》。不过剧本要更好一些。那达夫·拉皮德用有趣的小桥段展示出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即“本地人”和“移民”(注意是移民不是难民)之间的关系。移民用贬低自己祖国的方式迎合本地人的好感和关心。甚至表现得比本地人更加“本地”。片中男主多次赤裸。而本地人永远衣冠楚楚。移民用一切方式证明自己已融入新的国家。以至于自我麻痹到令人发笑的程度。却在获得新国籍之前迷失了身份。因为在本地人眼中移民永远是外来面孔。你可以是炮友但不会是丈夫。本地人对移民的故事失去兴趣。移民发现“外国”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最终本地人用高雅的古典乐压盖了质问。用紧闭的房门迎接拜访。移民身上永远背负着处于两种身份间的尴尬和矛盾。并失去自我认同。说到底。谁又比谁更虚伪呢。
莫名其妙/男主真的好憨啊
晦涩难懂,平淡无奇
1.选择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挺难的,因为活在现实世界里常会遇到各种不可控因素……2.办公室西装男打斗戏莫名有种 Men At Play 的感觉;3.看完才知道那达夫·拉皮德也是《教师 (2014)》的导演(不过我更喜欢翻拍版《幼儿园教师》);4.看豆列《1951-2019 德国柏林金熊奖最佳影片》和 【金熊奖】百度百科惊讶发现《仙履奇缘》获得1951年 第1届德国柏林金熊奖最佳影片?(一直记得《千与千寻》才是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于是查了下,《仙履奇缘》获得的是 Golden Berlin Bear Best Musical(最佳音乐片)、Audience Poll: Grand Bronze Plate(读者投票奖大铜盘奖)。貌似从1952年第二届才开始颁发如今的金熊奖最佳影片?……-9696 -19.08.27/28
观影情绪:哇露了!👉什么鬼👉哇夜店戏拍好好👉神经病啊👉模特裸戏棒棒!👉莫名其妙👉结束了。以色列反战小哥在融入过程中被利用拒绝的故事,隐喻外族融入过程中,所谓的“文明”不过是糖衣炮弹,接济也是抱着虚伪的目的,外族一旦极端发声便一脚踢开。PS:恭喜拿到金熊奖,和去年金熊一样开场几分钟就有大屌看。
纸上得来终觉浅,踏破铁鞋也只是在异国的门槛前盘旋。(看完在电影院门口看到张艾嘉,不知道她喜不喜欢这部电影
柏林电影节# 竟然是比較驚喜的一部。荒誕怪異淋漓盡致,什麼也不說和什麼都說了一些。
非常喜欢,摸在地毯下的那个钥匙让他丢失了所有,他以为找到了一扇打开的门,到头来那扇门从不会为他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