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拉斯》剧情介绍
阿尔卡拉斯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本片由加泰罗尼亚导演卡拉·西蒙执导,讲述了一个传统乡村家庭中桃子采集活动日渐式微的故事,当有人提出要将桃树砍伐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此适应新的方式时,这家人开始了捍卫自己土地的“战斗”。本片以使用非专业的加泰罗尼亚语演员为特色,于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作世界首映,并获颁最高荣誉金熊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杀人牛仔裤风声大人物已经开始想你爱情限时恋未尽被诅咒的土地一锤定音哈哈哈新年喜戏雀圣3自摸三百番谍影重重樟帮铁血男儿夏明翰复制品田耕纪纯白之恋二代宗师混沌之子SILENTSKY决不放弃水怪2:黑木林逃出熔炉陋室乐高DC沙赞:魔法与魔物九鼎记之禹皇宝藏杀漠神魂颠倒癫狂之旅第二季迪兹先生与光同尘浪漫暴风圈只在想死的夜晚
本片由加泰罗尼亚导演卡拉·西蒙执导,讲述了一个传统乡村家庭中桃子采集活动日渐式微的故事,当有人提出要将桃树砍伐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此适应新的方式时,这家人开始了捍卫自己土地的“战斗”。本片以使用非专业的加泰罗尼亚语演员为特色,于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作世界首映,并获颁最高荣誉金熊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杀人牛仔裤风声大人物已经开始想你爱情限时恋未尽被诅咒的土地一锤定音哈哈哈新年喜戏雀圣3自摸三百番谍影重重樟帮铁血男儿夏明翰复制品田耕纪纯白之恋二代宗师混沌之子SILENTSKY决不放弃水怪2:黑木林逃出熔炉陋室乐高DC沙赞:魔法与魔物九鼎记之禹皇宝藏杀漠神魂颠倒癫狂之旅第二季迪兹先生与光同尘浪漫暴风圈只在想死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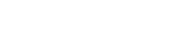
【于HKIFF49】张吉安对于母亲角色一贯的敏感有表达欲,叠加他最擅长处理的种族宗教冲突问题,对伊斯兰社会女性处境从第一帧开始即行批判。不过电影叙事的话题庞大就不好找重心,难免有些段落的节奏拖拉,两位女主的表演煽动力也比较一般 ,3.5…意外导演亲自到场,完成一场高质量的映后QA,补充了很多电影的创作背景,蜗牛戴胜鸟雌雄同体等等意象的解读,更加感受到他作为男性导演罕见的对女性的友善和反思,+0.5
SIFF27 看题材对它期待太高了 拍出来的不符合期待值
砍掉二十分钟对叙事毫无影响,冗余镜头多为形式服务,对故事推进毫无帮助,节奏一塌糊涂。偶尔闪现的亮眼镜头也缺乏应有的延展与呼应,浅尝辄止,浪费了一个本可以更有力的题材。(其实我最喜欢电影院手挡镜头那段
这部电影正是对“伪善的道德批判”的无声反抗。导演通过纪实风格,让观众直面问题,而非消费苦难:当社会拒绝帮助这些女性,她们只能依靠彼此
#HKIFF 三星半。弃婴舱是很好的题材,尤其在马来西亚这个多种族国家和Post-COVID的时代背景下。张吉安选取一种女性视角切入,对性别和母职的探讨杂糅着种族和宗教问题,其招牌式的魔幻/超现实段落(比如蜗牛和戴胜)和民俗部分有一种奇异的疏离效果(但也未必很有效)。总之我总幻想如果让怀斯曼从机构角度来拍一个关于弃婴舱的纪录片会不会更精彩?
#HKIFF49 电影院洗手间的那场哭戏简直是灾难……
明明去年《五月雪》就上过当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意象很多 也知道你要拿来做什么但这样搅成一锅粥 没有讲故事能力只是把现象摊出来 意义何在?
非常張吉安式的敘事,但其實已將「靈異」降到最低,且不斷用詩化的片段去橋接整個故事以及大馬多族中女性不同卻相似的困境。從多個角度去窺探大馬社會以及這個無解的話題,當搖籃中的嬰兒搖起他的小手,人心就被牽絆,而好的壞的回憶跟著形塑,但同樣的自私,保護,孤立也在侵蝕著人心。業的造就,便是如此形成,男性也好,族群也罷,甚至只是「網民」,作為暴力施加者,話語強加者以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的謊話編造者,完全不自覺,反而不斷地強化對立,才是社會最大的悲哀。
6.17 SIFF 映后
新知+1,困意+10
演员演技都不错
支持张吉安导演
比五月雪看得容易多了…
(hkiff 25/4/10)3.5 可能因为映前听导演讲了一些创作背景和想法,所以能感觉出故事还是有点儿意思的。但叙述如同马来西亚的语言系统,乱到让人有点头疼。
音乐最佳 还是符号法 为善良的男导演加分 看完登 再看这个解气
我觉得女一呆若木鸡😂但这并不妨碍两个女主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诡异的好磕。
好久沒看過這麼爛的電影了😒開頭幾個場景還拍得挺有feel,本來還有有點期待怎知接下來的劇情就猶如其他馬來西亞電影一樣毫不合理(光我散場跟朋友聊就可以挑出十幾個點出來了🌚)拍攝手法糟糕,然後很多情節設計是為了劇情推進而硬塞,本來還想為兩個很喜歡的女主(她們演出得很好)而禮貌三星,見過看到(又出現在馬來西亞電影)的qj橋段我真的不行了🌚故事出現這種情節本身不是問題,但他這樣呈現純粹就是想毫無意義且片面地噁心人🌚(想噁心人你學學熔爐好不)不行了,越打越氣,我給了很多次機會了(這次還拉了我朋友去看),馬來西亞電影掰掰最後再吐槽一點:説男人全部是壞這個主題沒問題,但你把所有男人角色除了片面的壞以外毫無屬性這樣咋說服人(生理女性都看不下去了)建議解決方法:改成GL
有人觉得反派选角失败,但我认为这种用力过猛的表演反而符合角色设定
选题很好,但有点拍烂了,好多部分都想快进。导演只是把主题带出来,完全没有深挖
节奏把控的不是很好/带着非常喜欢民俗和对导演高期待的前置条件,耐心去等故事节点,但看到的都是把议题放进作文中淡淡的疯狂,但是很喜欢结尾,这种把故事落点铺陈进形式性的展现,非常张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