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剧情介绍
都灵之马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随后,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跟我走吧巫咒跛子脚踏雪寻熊走过爱的荒蛮海豚踢盛装查理说逃出立法院有你的小镇:黄昏交叉点OAD2木乃伊狂鲨乐一通大电影:地球爆炸之日蛇女添丁异形:收割诸事不顺!未来预想图边缘服务津门三少爷樱花酒店致命密室穷途鼠的奶酪梦肖邦:爱的渴望蛇变火线干探之毁灭魔鬼时刻第一季绝命枪王RISKY巴黎恋人丛林奇兵鬼妇2:村庄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随后,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跟我走吧巫咒跛子脚踏雪寻熊走过爱的荒蛮海豚踢盛装查理说逃出立法院有你的小镇:黄昏交叉点OAD2木乃伊狂鲨乐一通大电影:地球爆炸之日蛇女添丁异形:收割诸事不顺!未来预想图边缘服务津门三少爷樱花酒店致命密室穷途鼠的奶酪梦肖邦:爱的渴望蛇变火线干探之毁灭魔鬼时刻第一季绝命枪王RISKY巴黎恋人丛林奇兵鬼妇2: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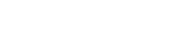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爸爸…” “我不知道” “吃吧” 风在近处刮得呼呼的,远处树木景物纹丝不动。鼓风机啊…同志们……
糟糕的实验电影,实在很难想象这是2011年的电影,阿克曼在70年代的实验影像都比它有先锋性。鲸鱼马戏团的长镜头还令人津津乐道,都灵之马的长镜头就只剩下了坐立难安,几欲先走的痛苦。同样是生活流的日常闷片,让娜迪尔曼比其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层。我没怎么看出来本片和尼采的关系,连反尼采也没看出来,神神叨叨的几句台词实在令人不适,我能感受逆七日创世神收回了光,但对于人类灵智未开时的野兽性展现也不够深刻。贝拉塔尔是不是不太会用影像来展现思想,两者没有一致大多数时候的两者都是混乱的,和马力克的影像哲学思想比起来差得太多。现在看来贝拉塔尔的电影缺少了力量与想象力。
#Curzon #二刷 25082024 长评-尼采与马的对视,西西弗斯推着石头。跟一刷时候的感受差不多,贝拉塔尔的灭世,荒诞的生活如同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否幸福取决于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接纳它。#MUBI #一刷 07072024开场小故事接着 一个老者赶着一匹马在狂风之中前行作为定场镜头,展现着一种“生活”。我认为整部电影与开场尼采的关联性在于,这个老者和他女儿所代表的是尼采抱住的“马”,而无情虐打马的马夫则对应着大环境,那狂风,那枯井,那生活。而尼采这个表达出“上帝已死”言论的哲学家似乎就像是拥有上帝视角般的观众,来看着这对父女在经受苦难却无所作为,也无能为力,只能啜泣。太喜欢第五天和那匹马对视的镜头了,似乎一个轮回,那静静的对峙,看到他的苦难,就如同它是这对父女,是我,都灵之马。
讲述了一位马夫和女儿六天的各种艰难生活。他们和马夫的那匹都灵之马无本质区别,都是在大环境下苟延残喘。所以在开头引言中当马夫鞭打马时,尼采失声痛哭。②各种《鲸鱼马戏团》式浸入式长镜头(最喜欢开头策马扬鞭的长镜头,完全是教科书般的关于「马在人的压迫下艰难求存」的视听交响乐),也和《鲸》一样渲染了深沉悲悯的氛围,这种气氛还通过生活流叙事和大量运用重复场景来增强。《都灵之马》
这么苍白的色彩却带来强烈的震撼
不喜欢配乐的用法。但是故事却非常好,这就是所谓的文学长镜头么?
导演说:“快看我的画面,看这构图明暗是不是很美!”看了半个小时,“快听我的配乐,是不是很碉堡!”听了半个小时,“快看我的故事发展,是不是很有寓意!”然后重复一遍…以上即所感,为了不拖欣赏水平后腿,五星…
从玩游戏的角度来说,这可以理解为大师版本的“八号出口”:影片看似每天做的事情一样,但每个细节都不一样,需要你在重复中找到不同和端倪。尼采是个精神极丰富的人,表现形式却极其贫乏,可谓是一种冷酷的批判。
惯性的平静没有时空对比,你就不应该谈悲苦,你觉得洞穴里的原始人有多少焦虑?美是俯视我的东西,我不自卑也不迎合,只有安睡
生活是无聊,是重复,是失落,是困倦,还是睡着以后的梦,即使整个世界已然崩塌。[小记:《都灵之马》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结束的地方]
上个厕所回来之后,发现镜头都不会变的那种电影……
我有空长镜无冲突恐惧综合症再大师也不行。
尼采,寒冬中赶路的马,黑白画面如同一幅静物画,一个残臂的马夫一个女儿一匹马,呼啸的寒风,无声,(哲学电音都很符合实验影像风格),低沉的音乐.马即人,马不吃东西不愿走动亦如人最后的境况。都灵之马既是都灵之人,面对生活的艰辛,都灵之人作为尼采式超人存在的失败。
撒旦探戈看了十年都没看完。。。已经对这个导演有阴影了,鼓起勇气点开都灵之马,这是塔尔版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开场马的长镜头是真漂亮,不过整部片子太形式主义,而且炒得还是撒旦探戈的冷饭,台词说教直给。如果十年前我看这部片子可能惊异于影像创作的包容度,但现在,真的不喜欢言之无物的东西。也不能说他什么也没讲,只是表达出来的内容太直白太简单了。看完想给《上帝难为》加一星……
我道行不够,还没看出个倪端。就觉得导演很大气。现在是3个月后,这个影片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造化太浅,欣赏不了,只觉得催眠......大荧幕根本不适合这么直白地讨论哲学问题,然后也没看出父女俩日复一日琐碎无味的生活细节和尼采哭马这一命题之间迂回的内在联系。
这他妈简直像极了我的生活,我也想问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個人在不擁擠的電影院觀看,可能會加上一星。整體感覺因為和不久前看過的撒旦探戈不由自主在做對比,所以很難有更高評價。當然,亮點貫穿始終。在重復中的變化最吸引人。
《都灵之马》将台词缩减至最低限度而产生大量的留白,透过长镜头所不断重复的生活场面来表现生活的枯燥无味的永恒轮回,如同屋外呼啸的寒风:几乎毫无故事情节的发展表象下实际是走向毁灭的过程,马,作为影片的旁观者也类似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角色而成为尼采的象征。人类亟待被超越。正午前的末日
说好听点,你是孤芳自赏,说不好听的,你是脑壳空空,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