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天空》剧情介绍
红色天空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一个炎热、干燥的夏日,如同过去几年一般。森林火灾是无法控制的。四个年轻人在离阿伦斯霍普不远的波罗的海度假屋里相遇。慢慢地,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火焰筑成的围墙所包围。红色的天空笼罩着他们。他们充满怀疑,他们满是害怕——但却不是因为火灾。是爱让他们害怕:“谁会在坠入爱河时死去 ……!”他们越来越亲近,他们渴望着,他们相爱着。然而熊熊火焰已无限逼近。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可爱的中国杀戮开始巴黎五区的女人杀寇决漠风吟美丽的真相至诚感天那一天好男儿之情感护理毕业作品切肤之痛第二季副作用烈血暹士魔卡少女樱透明牌篇蜜月大明风华黄真伊艳妇突务齐欢唱罗宾汉纸牌屋第三季浓情酒乡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歌剧院最后的杀人机甲英雄机斗勇者名厨卡雷姆无边泳池黄阿丽:小眼镜蛇恶灵交响曲我的魔法预言银魂:最终篇人间蒸发
一个炎热、干燥的夏日,如同过去几年一般。森林火灾是无法控制的。四个年轻人在离阿伦斯霍普不远的波罗的海度假屋里相遇。慢慢地,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火焰筑成的围墙所包围。红色的天空笼罩着他们。他们充满怀疑,他们满是害怕——但却不是因为火灾。是爱让他们害怕:“谁会在坠入爱河时死去 ……!”他们越来越亲近,他们渴望着,他们相爱着。然而熊熊火焰已无限逼近。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可爱的中国杀戮开始巴黎五区的女人杀寇决漠风吟美丽的真相至诚感天那一天好男儿之情感护理毕业作品切肤之痛第二季副作用烈血暹士魔卡少女樱透明牌篇蜜月大明风华黄真伊艳妇突务齐欢唱罗宾汉纸牌屋第三季浓情酒乡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歌剧院最后的杀人机甲英雄机斗勇者名厨卡雷姆无边泳池黄阿丽:小眼镜蛇恶灵交响曲我的魔法预言银魂:最终篇人间蒸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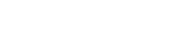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被创作焦虑裹挟,缺乏对外界感知力的无能作家的一段经历,关于自身感知与外界变化错位、爱欲“震动”、青春、艺术、自然和死亡的故事本来很高级,但这样一位男主角实在使人缺乏共情兴趣。人物之间的矛盾,突然发现自以为是卖冰激凌的草包女人原来是文学研究准phd之类情节点设计也有一种小品式的毛糙刻意。
平静如深水湖之下掩藏着浓烈到窒息的情愫,完美的文学性又仿佛发生在平行世界的故事,爱情从未如此动人深邃,死亡从未如此刻骨凛冽;柔软的心经由无常世事匕首雨般的洗礼,方能长出足够粗糙坚硬而举重若轻的保护壳;从薄如白纸到岁月沉淀,从轻佻错过到释怀重逢,此刻再见昨日的自己,大概已恍若隔世般幼稚遥远了。
当你以为全世界都针对你时,试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过于男本位思考这个世界了?Who asks you?
两星给导演技法 就是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女性为什么会疑似喜欢上这个男主 这男主的人格有任何有魅力的地方吗 从头到尾招人烦 有女性观众会感同身受吗?
片头片尾音乐挺好啊。
#73thBerlinaleWettbewerb#用文本叙述的情感张力去试图逼出视点镜头的异质时刻,这是佩措尔德从《过境》开始就一直在尝试的创作方式。《红色天空》的突破更多是在类型上,这固然是一种更商业化的尝试,但杰出的剧作还是让故事最终来到了熟悉的佩措尔德电影时刻。
@2024-06-02 12:36:47
这部电影活脱脱地像导演和编剧的反面教材,究竟是我看不懂了,但很佩服导演的勇气and它是导演拍了十二部片子后出来的作品
从头到尾都好无聊好cliche……感觉从前15分钟开始就能猜到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山火灰突然出现那里还以为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画面和情节,但没想到等待我的是脑瘤骤死和坂本龙一……同样是“探索男性自私的小世界”,然而还不如《晚安步步》半卷……然后男主tm写了本破小说就能被救赎了?真是白左圣母心。总而言之,挖得太浅又故作玄虚,看得我属实有点恶心
比温蒂妮更喜欢,佩措尔德加葆拉贝尔的组合真的是绝了,悄无声息寥寥几笔就构建出暗潮涌动的角色和人物关系,烈火炙热的将大海也蒸腾,倒映出惊心动魄的红色天空。
年度场景:Nadja 拿着透明杯子从小屋走出,置身于悬浮的山火灰烬中,身后是一片蕨,她穿红色。
3.5 余韵很长,但需要花点时间把导演的叙述能力和恼人的白男小胖区分开来,有点不知道怎么评价,情绪很连贯很流畅,一切都介于说与不说之间。
Paula第一次出鏡便以拒絕諂媚的背影騎往外部世界。正如導演所説林中小屋和這個asshole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隱含的另一層邏輯是創作者選擇不(或者無法?)在女性視角建立敘事時,依然可以以她作爲「健全人」的參照把巨嬰駡到狗血淋頭。佩措爾德說 dystopian movie 自帶一種「一把火把世界燒光再重頭來過」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但在這類電影中,他也想呈現出真實世界的複雜面向。能夠見證他的創作軌跡,是一種幸運。
变gay喷雾和林火意像(但没用好)两星
没有天空,也不火红;实在不知道拍摄一个渴望认可、嫉妒他人却又极其自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能男性有何意义,也许意义就在于让人写出一样自视甚高的影评;除去男主,皆是能看的剧情和还算有趣的片段,尤其葆拉·贝尔的 Nadja 和 Felix 都算有趣的角色,但是男主的戏份实在如鲠在喉般的难看
余味悠长,最后的收尾与点缀让整部电影变得更生动更深情。从只考虑自己工作总是独自行动到开始观察和感受当下生活,这段时间里他错过了朋友间的交谈欢笑,错过了了解他人的机会,错过了夜晚会发光的大海,最后抬头只看见那片红色天空和被带走的那对爱人。
可能我跟佩措尔德真的八字不合,这个躁郁作家通过烧死同性恋(literally)来获得创作灵感的寓言故事让我完全无法共鸣。不过作为元素三部曲之二,人心的焦灼和山火的失控互为表里,确实把火的象征性诠释到了极致。
纯纯浪费时间。udine比这部好得多。女主倒是一如既往地好。
恕我没心情体会这个胖子的熬糟心情跟蹩脚情绪。那是我观者的问题吗?我需要自责没有沉浸的心吗?
非常不一样的佩措尔德电影,游戏感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