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比勒》剧情介绍
西比勒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西碧勒(维吉妮·艾菲拉 Virginie Efira 饰)曾经是一名心理医生,却因为实在是太过于热爱文学创作,而最终选择放弃做医生,一心扑到了写小说上。一次偶然中,西碧勒邂逅了名为玛格特(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 Adèle Exarchopoulos 饰)的女子,玛格 特是一名女演员,正身处于情感纠纷之中无法自拔。 玛格特参演了一部电影,却怀上了男主演伊戈尔(加斯帕德·尤利尔 Gaspard Ulliel 饰)的孩子,而伊戈尔和这部戏的导演是情侣关系。这段复杂的三角恋让玛格特痛苦无比,对西碧勒掏心掏肺,而西碧勒则偷偷录下了两人的谈话,作为创作小说的灵感。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黄沙渡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性爱之后谍影重重3重返芳园灰色气流百折不挠具海拉永冬执着的追踪老大夫小大夫光环:夜幕校花诡异事件诊疗中第一季实习医生风云第七季淡蓝琥珀圆圆的故事孤国春秋第二季狼人花园外星萝莉变脸侠1993空劫行动无底洞拿纳克宗师号事件家庭县委大院阿马尔菲:女神的报酬回声源头百年的新娘人生需要揭穿零度战姬
西碧勒(维吉妮·艾菲拉 Virginie Efira 饰)曾经是一名心理医生,却因为实在是太过于热爱文学创作,而最终选择放弃做医生,一心扑到了写小说上。一次偶然中,西碧勒邂逅了名为玛格特(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 Adèle Exarchopoulos 饰)的女子,玛格 特是一名女演员,正身处于情感纠纷之中无法自拔。 玛格特参演了一部电影,却怀上了男主演伊戈尔(加斯帕德·尤利尔 Gaspard Ulliel 饰)的孩子,而伊戈尔和这部戏的导演是情侣关系。这段复杂的三角恋让玛格特痛苦无比,对西碧勒掏心掏肺,而西碧勒则偷偷录下了两人的谈话,作为创作小说的灵感。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黄沙渡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性爱之后谍影重重3重返芳园灰色气流百折不挠具海拉永冬执着的追踪老大夫小大夫光环:夜幕校花诡异事件诊疗中第一季实习医生风云第七季淡蓝琥珀圆圆的故事孤国春秋第二季狼人花园外星萝莉变脸侠1993空劫行动无底洞拿纳克宗师号事件家庭县委大院阿马尔菲:女神的报酬回声源头百年的新娘人生需要揭穿零度战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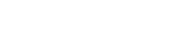
现实、小说、电影、心理治疗的的多层指涉,还有斯特龙博利火山的影史级引用,剧本太精彩了,可惜结尾差了一口气
第一句就很有意思,读者是作家的人质。其实作家、心理医生、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个觊觎他人生活的旁观者,都在观摩,吸食,消化,自我感动,有的人对文字、影像、他人故事或自我想象上瘾,会有越界的狂喜与折磨。不新鲜的故事,但演员与表演赏心悦目。三星半。@法国影展
精神分析师与精神病人,现实与回忆;精神分析师与小说家,现实与虚构;随后人物介入拍摄现场,虚实之间,情绪倒置。
#资料馆#层次太过分明的虚构,只有某些视点是新鲜的,上岛后的奇遇(或蔑视)式影像是心理的极度外化,爆发于意义明确的高潮蒙太奇,这一段落本身说实话有点cliche了,好在桑德拉女士用强大的表演将其拉入了一种荒诞的无语气的语境,所以这其实又是最好的部分。后日谈和结束语最糟糕,像是一种与小说对仗的执念,“我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这种宣言只有结构性的作用,何必总结。
《坠落的审判》导演的前作,目前评分绝对低了。因为对于女性细微心理转变的刻画极为传神。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如此尺度的激情戏,看得人是面红耳赤。本片女主角之一是《阿黛尔的生活》的女主。
又名,《心理醫生與她的自我戲劇》,讓人聯想到歐容的《池畔謀殺案》,已經不是區辨現實與虛構的問題,而是虛構就是還沒實現的現實,而現實轉瞬成為紙上虛構,乍看瑣碎實則精密的劇情結構,讓人看完,初不覺如何,但越回味的時候就越感到意猶未盡,影后桑德拉的參與給本片增添奇妙風味,只有女性才能拍出來的細緻電影。
受不了法国人这种不好好说话的片子
3.5。前面的吸引点在于悬念,一个越界了的心理分析师将会引出多大的乱子;后面变成了发生在戏内戏外的三角恋,Sandra Huller饰演的导演承担了绝多数的喜剧色彩。情节发展的有点难以预料,表面上看去也好似并无章法,甚至剪辑节奏也很怪异。
6/10.只有情绪,没有叙事。
刚开始看觉得剪辑很跳跃,有点理不清每条线都在干嘛。看完后回头一想,其实各条线都很清晰。刚开始看似混乱的剪辑像是按西比勒头脑中的场景来展现的,她想到哪,我们就跟着看到哪。她回忆着的过去,并作为心理咨询师听着阿黛尔的故事,又去见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将阿黛尔的故事混合着自己的故事写进小说,各个层面的故事都有了。最后小说有了,回忆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都面临着失去爱。
导演把这么一个略狗血的故事通过回忆和现实、电影、小说、心理治疗拼贴剪辑在一起,技巧厉害,看得津津有味。
什么购机吧
真是烧脑片,想的全是这个和那个啥对应?她也这样?抛开这些,单从视听上讲确实是好看好听的
刻意散碎割裂的剪辑模糊了真实与幻想的边界,由此而生出的迷乱和惶惑倒也与剧情相得益彰。
低配版欧容。
通过心理辅导她人的形式完成自我治愈,经历的雷同让两个女人成为彼此的映射,只不过因为一个决定的不同,最后驶向了不同的结局,很明显影片想走那种偏心理探究层面的类型,不断的闪回和现实纠结在一起完成对记忆深处的回溯,可惜一切看上去还是矫饰了一些,剪辑也比较碎,无法引起共情。
?意思就是可以随便乱搞,只要搞完悔过就行了?
3.5/剧本不错,非线性却不乱,结尾没太收好
一个做过心理医生的作家,在创作和现实之间,苦苦挣扎。自己没疯,难得。
几位复杂的女性形象正如埃菲拉面前的回转寿司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罗西里尼的火山与高达的大海在此合体绽放,打乱线性时空,虚构与现实,喜剧也愈加好看。